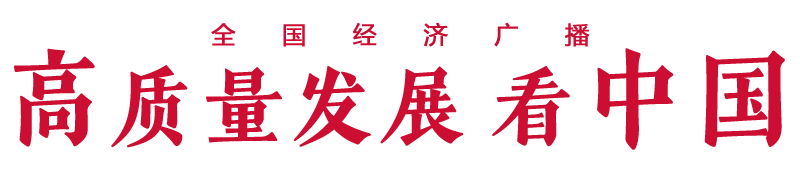文/张毅龙
一、行道于今:古道的现代体温
晨光熹微,我展开那卷微缩的竹简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。油墨的气息与屏幕的冷光悄然融合,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静静浮于眼前。我不禁思索:这部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烽火与动荡中的典籍,那套玄远的“四维世界”构想,在信息奔涌、步履匆匆的今天,究竟何为?它仅是陈列于思想博物馆的标本,还是依然流淌在我们血脉深处、等待被重新认领的活水?
老子所说的“道”,先天地生,独立不改,周行不殆。它并非人格化的造物主,而是一种“自本自根”的宇宙法则,核心是“自然”与“无为”。尤为深刻的是,老子将此天地之“道”与人伦之“治”、个体之“心”贯通一体。在他眼中,社会失序与人性异化的根源,恰在于背离了“道”的清净本性。因此,回归于“道”,便是治愈时代症候的一剂古老药方。
将目光从宏大叙述收回,投向自身被焦虑填满的日常,老子的智慧首先呈现为一种“心灵哲学”。在欲望的迷宫中,“道”教人“知足寡欲”,警醒那些被不断煽动的“人为之欲”;在人际的纠葛里,“道”启示“柔弱不争”与“和光同尘”,似水般“善利万物而不争”;在功名的追逐中,“道”劝诫“为而不恃,功成身退”。这不止是明哲保身的世故,更是一种“生而不有”的生命境界。
其治理思想的精髓在于“无为而治”,强调信任并激活社会内在的生机。而“小国寡民”的愿景,则寄托了对和平、淳朴、自足的共同生活之深切向往。置身全球化浪潮,老子的思想更凸显出跨越文明的普世意义。“大道之国”当“道法自然”,于国际交往中“利而不害,为而不争”,倡导一种基于平等与尊重的世界秩序。
暮色四合,我合拢书页。窗外都市华灯初上,车流如河。老子笔下的静好田园,似乎与眼前的钢铁森林格格不入。然而,“道”的精魂却仿佛穿透厚重的时间,在此刻显得愈发清晰而迫切。
我们所需,或许并非复现结绳记事的古老形制,而是重拾对生命本身的敬畏,对自然律动的尊重。这条路,值得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民族共同探寻与实践。
二、归途灯火:乡愁的当代形状
每个中国人的行囊深处,都叠放着一阕属于故乡的词。它或是贺知章鬓边的霜雪,或是王维窗前的寒梅,更多时候,它是张籍手中那封拆了又封、总也写不完的家书。
春运站台上,他挤在涌动的人潮里,忽闻一句熟悉的乡音。回首望去,一位背着蛇皮袋的老人,正用他儿时的土话对着手机低语。那一刻,五十载光阴坍缩为一声轻唤——他恍然惊觉,自己也成了贺知章诗中那个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客子。故乡以方言认出了他,却用陌生的街巷温柔提醒:你已是归来之人。
他在异乡高楼的玻璃窗边,养了一盆梅花。深夜里,屏幕上数字如星河流动,他总会记起王维那句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。老屋早已不在,唯有童年手植的那株梅,依然在每个腊月将幽香送入梦境。他不再追问故乡变了多少——只想知道,穿过巷弄的梅香,是否还似当年清冽。
乘机穿越云海时,他总选靠窗的座位。一次夜航,见皎月静浮于雪峰云涛之上,忽然懂了李白出蜀时那一眼回望。原来人人心中都悬着一轮“故乡月”——也许是门前的枇杷树,是小学操场边的槐花。我们背着这枚月亮行走世界,在纽约地铁、伦敦夜雨、东京便利店的灯光里,悄悄比对它的阴晴圆缺。
更年轻的一代,渐渐在异乡扎下根须。他们借外卖点选家乡味,于短视频里看故里春秋,却越来越怯于点开那句“何时回来”。韦庄的词被悄然重写:“人人尽说他乡好,游子只合他乡老。”非是不愿归,而是归途难——孩子的学业、未稳的职业、不敢松懈的日程。故乡成了春节限定的童话,七天后,一切恢复原状。
可总有某些时刻,乡愁会刺穿所有屏障骤然苏醒。或许是地铁里孩童一句方言的追问,或许是货架上偶然出现的童年零嘴——就像崔涂在乱山残雪中望见的那盏孤灯,亦如马致远笔下那匹驮着夕阳的瘦马,瞬间洞穿现代生活坚硬的壳。
我们这代人,成了史上最矛盾的游子:离故乡越来越远,舌尖却借由物流与故土紧紧相连;指尖能触及世界任一角落,双脚却数年踏不上那条回乡的小径。纳兰词里的风雪声,如今化作微信视频的卡顿、那句“一切都好”背后不易察觉的叹息。
然而正是这亘古的乡愁,让我们在算法的茧房中,依然记得自己是哪一片土地长出的穗;在标准化的滋味里,仍能辨出故乡水土独特的印记。柳宗元“若为化得身千亿”的祈愿,今日以另一种方式实现——我们的乡愁散落云端,化作朋友圈里故乡的云,美食视频中的家乡味,地图上那颗始终闪亮的坐标。
夜深时,他常独自走上天台。城市灯火如倒悬的星河,而在星河最深最远处,他知有一盏灯属于故乡。就像戴叔伦在石头驿遇见的那盏寒灯,它静默无言,却已回答所有:关于为何离去,关于为何坚持,关于一切远行终将指向的归途。
三、道在途中:行走与回归的双重奏
原来,我们所携的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地点,而是一枚精神的胎记。它是贺知章未曾更改的乡音,是王维年年追问的梅讯,是张籍手中未竟的家书,也是我们相册里永不删除的旧影。在这个高铁取代鞍马、微信代替尺素的时代,乡愁依然保持它古老的姿态——永远在抵达的途中,永远在启程的刹那。
而所有中国人,无论走出多远,始终走在同一条归途上:从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的怅惘,走向“应知故乡事”的坦然;从“望极天涯不见家”的彷徨,走向“散上峰头望故乡”的释然。
故乡从未真正遥远——它就在我们说话的声调里,在舌尖的记忆里,在每一个“复恐匆匆说不尽”的欲言又止里。我们都是张籍,在人生的秋风之中,不断书写那封永远写不完的家书。拆了又封,封了又拆,并非词穷,而是那份心意,始终如初,万重难尽。
灯火渐次亮起,照亮每扇窗后的孤影。从三峡的驿栈到星城的公寓,从高原的夜航到越洋航班的经济舱,变换的是舟车形制,不改的是那颗“聒碎乡心”的寂寥。而所有出发,最终都只为确认一事:无论成为多么合格的“异乡人”,我们灵魂的籍贯栏里,永远写着最初出发的那个村庄、那条小巷、那方院落。
那里,始终亮着一盏灯,如李觏诗中虽被暮云遮蔽却长存天际的落日,它轻轻说着:所有天涯,皆是归程的起点。
四、大道归一:智慧与乡愁的精神合流
当我们将老子的“行道于今”与游子的“灯火归途”并置,一条隐秘的精神线索逐渐清晰:在东方智慧中,“道”的追寻与“乡”的眷恋,本质上是同一种生命姿态——对根源的敬畏与回归。
《道德经》教导“复归于朴”、“复归于婴儿”,那是精神的还乡;春运人潮、窗前梅花、云端明月,那是情感的归途。在老子看来,背离“道”的世界是一个失乡的、异化的世界;而在游子心中,远离故土的人生总带着一份难以名状的漂泊感。
疗愈现代性焦虑的“道”,与安放漂泊心灵的“乡”,在深处相通。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对完整性、本真性的渴求,以对抗生活的碎片化与工具化。知足寡欲、和光同尘,何尝不是在精神上“回家”的修行?而对故乡风物固执的怀念,又何尝不是对生命本然状态——“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”——的天然向往?
在此意义上,践行古老智慧与守望精神故乡,实为一体两面。我们一面依“道”而行,在喧嚣中持守内心的清静与自然;一面怀“乡”而活,在流动中确认生命的来处与底色。前者为我们提供行路的智慧,后者为我们点亮归途的灯火。
当最后一缕天光没入城市轮廓,老子沉静的话语与游子缠绵的乡愁,在这个黄昏完成了跨越千年的对话。它们共同告诉我们:无论科技如何迭代,时空如何压缩,人终究需要一条“道”来指引前行,需要一盏“灯”来照亮归途。
而这“道”与“灯”,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那个我们从未真正离开,也终将回去的、完整而本真的生命原乡。在那里,行道即是归途,启程已是抵达。

作者简介:张毅龙,湘人,曾务农、做工、执教,诗文散见各媒体。